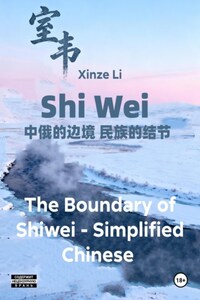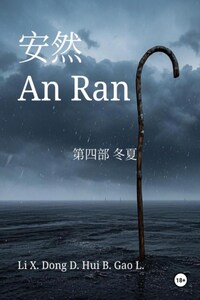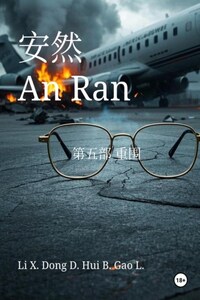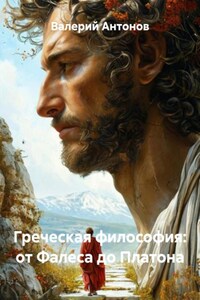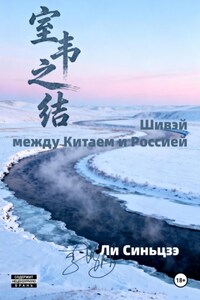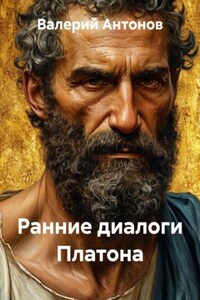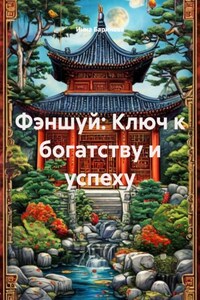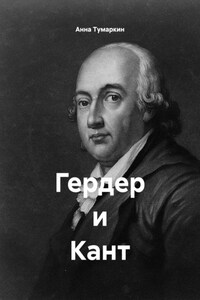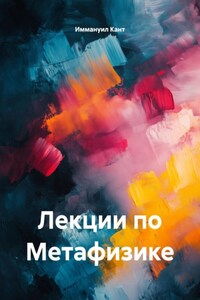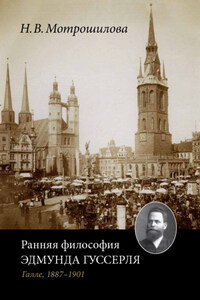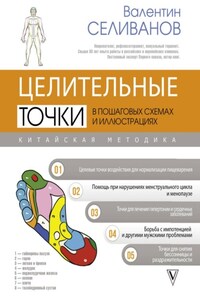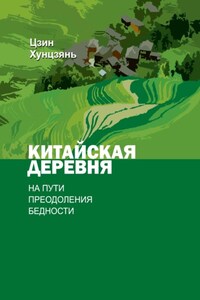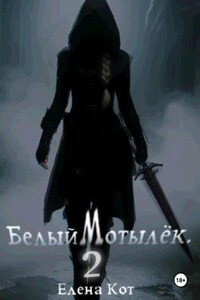张军坐在北京老旧公寓的落地窗前,指尖还沾着半块糖油饼的油星子。那糖油饼是楼下早点铺买的,外皮炸得酥脆,咬下去能听见“咔嚓”一声,内里却软乎乎的,裹着一层厚厚的白糖,甜得能糊住舌尖。他已经吃了两个,胃里沉甸甸的,像揣了块浸了油的海绵,但他的手还是不自觉地伸向了桌上的油纸袋–那里还有最后一个。
张军,四十二岁的年纪,体重早就过了标准线。圆脸,双下巴,肚子挺得像揣了个小皮球,走路时身上的肉会跟着轻轻晃动。熟人见了他,总打趣说“张军同志发福了”,他只能笑着应和,心里却清楚,这不是简单的发福,是过度进食喂出来的空洞。就像现在,窗外的都市街巷被灰蒙蒙的雾霾罩着,高楼挤着高楼,电线在天空中织成密不透风的网,连阳光都得费劲儿才能从缝隙里漏下几缕,落在楼下斑驳的墙面上,又很快被阴影吞噬。这种窒息感,他太熟悉了–就像他每次把食物塞满嘴巴时,喉咙口那种又满足又压抑的感觉,像一块湿抹布堵在那儿,吐不出来,也咽不下去。
他是“国际知名自媒体博主”,这头衔是他辞职后自己给的,后来被一些媒体引用,慢慢就传开了。每次介绍自己时,他都能感觉到这几个字里的虚浮–“国际知名”,到底多知名?是在海外社交平台有几百万粉丝,还是能接到几个跨国品牌的广告?其实都没有。所谓的“知名”,不过是他在央视做驻莫斯科记者时攒下的一点老本,是那些年跑遍俄罗斯大小城市写下的报道,是镜头里定格的克里姆林宫的雪、贝加尔湖的蓝、圣彼得堡冬宫的金色穹顶。可现在,那些都成了“过去式”。
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,手腕上还戴着当年在莫斯科买的那块机械表,表盘已经有些磨损,指针在“10:17”的位置轻轻跳动。十年前,他就是戴着这块表,拎着行李箱从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起飞,回到了北京。那时候,他刚从中国央视辞职,心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–他想做更自由的新闻报道,想把那些在央视没能说透的故事,用自己的方式讲给更多人听。可十年过去,他活成了自己最不喜欢的样子:每天盯着自媒体视频网站后台的流量数据,为了一个耸动的标题熬到凌晨,把原本需要三天才能写完的深度分析,压缩成三分钟的短视频,还得在开头加上“这个视频将会改变你的一生”“我很震惊!”这样的话。
“你老了,张军。”张军心底的声音又响了起来,清晰得像有人在耳边说话。这不是疑问句,是陈述句,这些话语非常寒冷,冷得像莫斯科冬天的风,刮在脸上生疼。他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,皮肤松弛,眼角有了细纹,手指按下去,能感觉到皮下的脂肪在轻轻晃动。这不是生理上的“老”,是精神上的枯萎–就像他阳台上那盆绿萝,自从他懒得浇水后,叶子一点点变黄,藤蔓软塌塌地垂下来,再也没有过生机勃勃的样子。
两年前不是这样的。那时候,他的国际评论博客还像互联网上的一座灯塔。每天早上醒来,后台能收到几百条留言,有人说“张军同志的分析太透彻了”,有人说“因为你的文章,我开始关注俄罗斯的历史”,还有人把自己拍的莫斯科街景发给她,说“这是我按照你写的路线去的,真的很美”。那时候,他享受那种“权力”–不是职位带来的权力,是用文字和镜头塑造公众认知的快感。
张军记得有一次,他写了一篇关于俄罗斯卫国战争老兵的报道,里面提到一位叫伊万诺夫的老兵,一辈子都在守护着家乡的纪念碑。文章发出去后,有读者专门从国内飞到俄罗斯,找到了那位老兵,还寄给张军一张两人的合影,照片里,老兵握着读者的手,笑得满脸皱纹。那时候,他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,就像在黑暗里点亮了一盏灯,不仅照亮了别人,也温暖了自己。
可现在,希望的灯灭了。
张军拿起桌上的平板,屏幕亮起来,映出他圆润的脸。最新一条视频是三天前发的,标题是“俄乌边境历史溯源:从克里米亚到顿巴斯,百年争端背后的真相”。他花了整整一周时间查资料,还翻出了当年在莫斯科采访时的笔记,视频里用了很多老照片,还有他自己拍的边境风景。可后台数据惨不忍睹:播放量刚过五千,评论区只有二十几条留言,还大多是“视频太长了,没看完”“直接说谁对谁错就行”“这个视频也太无聊了”这样的话。
他滑动屏幕,手指在那些评论上轻轻划过,像在触摸一块冰冷的石头。他想起自己为了“迎合”,做过的那些妥协:把“俄罗斯文学中的苦难意识”改成“3分钟看懂俄罗斯文化”;把“莫斯科地铁的建筑艺术”的视频剪成“盘点莫斯科地铁里的摄影点”;甚至在一条关于俄乌冲突的视频里,故意加入了“中美阴谋论”这样的表述–他知道这话不客观,可当时后台的播放量数据一直在掉,他急了,像个溺水的人,抓住什么都想当成救命稻草。
每一次妥协,都像在他心上划了一刀。白天,他看着上涨的播放量,会有一丝短暂的窃喜;可到了晚上,躺在床上,黑暗里那些被他修改过的文字、被剪辑得支离破碎的镜头,会一遍遍在他脑海里回放。
“坚守良知承受苦难,还是屈从欲望获得解脱?”这个问题像一根尖刺,扎在他的心里,拔不出来,也咽不下去。这两年,他一直试图屈从欲望,可解脱在哪里?没有。反而像陷在泥沼里,越挣扎,陷得越深。他的胃里又开始隐隐作痛,是刚才吃的糖油饼在作祟。他起身走到厨房,打开冰箱,里面塞满了食物:半只酱肘子,一袋速冻饺子,还有昨天买的烤鸭–鸭皮已经不脆了,泛着一层油光。他拿出烤鸭,扯下一块肉塞进嘴里,鸭肉的香味在舌尖散开,可那种满足感只持续了几秒钟,随后而来的,是更深的空虚,像潮水一样,从胃里漫到胸口,压得他喘不过气。
“够了。”他低声说,声音很轻,却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坚定。不是情绪激动时的脱口而出,是经过无数个夜晚的挣扎、无数次自我拷问后,得出的结论–笨拙,却诚恳。他回到客厅,拿起平板,点开自媒体账号的后台。注销账号的按钮在屏幕的最下方,灰色的,像一块墓碑。他的手指悬在上面,停顿了几秒钟–想起第一次发视频时的紧张,想起收到第一条好评时的激动,想起那些因为他的内容而产生共鸣的读者。可这些,都已经成了过去。
他按下了“确认注销”。
屏幕上弹出“账号已注销”的提示,白色的字在黑色的背景上,格外刺眼。那一刻,他突然觉得浑身轻松,像卸下了一块压了他好几年的石头。窗外的都市街巷,好像也失去了之前的压抑色彩,灰蒙蒙的天空里,透出了一丝微弱的光。那些挤在一起的高楼,那些织成网的电线,突然变成了一块巨大的、灰色的背景板–他想逃离这里,逃离这个被数据和算法绑架的世界。
张军决定去环游全国。他需要逃离,需要用身体的移动来对抗精神的停滞。他翻出了衣柜最深处的那个黑色背包,那是他当年在莫斯科当记者时用的,背包的带子已经有些磨损。他把心爱的摄影设备装了进去:一台用了五年的单反相机,两个镜头,还有一个笔记本–不是电子的,是纸质的,封面是牛皮的,已经被磨得发亮。这次,他明确告诉自己:镜头是用来记录“纯净生活”的,不是用来变现的;笔记本是用来写心里话的,不是用来写爆款文案的。
出发前的晚上,他把公寓里的食物都收拾了。糖油饼、酱肘子、烤鸭,还有冰箱里的速冻饺子,都装进了垃圾袋,扔进了楼下的垃圾桶。看着垃圾桶里鼓鼓囊囊的袋子,他突然觉得,自己好像扔掉的不只是食物,还有那些用来掩盖空虚的“填充物”。他洗了个澡,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,躺在床上,第一次没有失眠。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,在地上洒下一道细长的光,像一条通往远方的路。
第二天一早,他开着自己那辆用了八年的SUV,驶出了北京。车窗外的风景一点点变化:高楼变成了低矮的平房,柏油路变成了乡间小道,空气里的雾霾味消失了,取而代之的是泥土和青草的清香。他打开车窗,风灌进来,吹在脸上,带着一丝凉意,却让他觉得格外清醒。他没有设定具体的路线,只知道要往南方走–他在书里看过,南方有很多古镇,青石板路,小桥流水,像一幅水墨画。他想在那里找到一点“纯净”,一点能让他的心静下来的东西。
旅途的第一站,是南方的一个古镇。名字他记不太清了,是在导航上随便找的,据说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。可刚到古镇门口,天空就下起了雨。不是倾盆大雨,是那种细密的、连绵不断的雨丝,像无穷无尽的细针,从天上落下来,把整个世界都包裹在一种灰暗的、粘腻的氛围里。
他撑着伞,走在青石板路上。雨水打在伞面上,发出“沙沙”的声音,像无数只小虫子在爬。脚下的青石板路被雨水泡得发亮,坑坑洼洼的地方积了水,倒映着路边昏暗的灯笼光–红色的灯笼,被雨水打湿后,颜色变得暗沉,像褪了色的旧伤疤。他拿出相机,想拍一张雨中的古镇,可镜头刚对准前方,雨丝就落在了镜头上,形成一层薄薄的水雾,拍出来的照片模糊不清,像隔着一层毛玻璃。
他擦了擦镜头,再拍,还是一样。那些他想象中的“美”–小桥下的流水,白墙上的青瓦,门口挂着的红灯笼–在雨里都失去了光彩。流水是浑浊的,青瓦上沾着青苔,红灯笼耷拉着,像没精打采的病人。他沿着石板路走了一个多小时,相机里只存了几张模糊的照片,心里的挫败感像潮水一样涌上来。他意识到,他无法在潮湿中找到纯净–就像他无法在空虚中找到满足一样。
天黑的时候,他在古镇里找了一家民宿。民宿是老式的四合院,院子里种着一棵桂花树,叶子被雨水打湿后,绿得发黑。房间在二楼,推开房门,一股霉味扑面而来,混合着墙角青苔的味道,呛得他忍不住咳嗽了两声。房间里的家具很旧,一张木床,一个掉了漆的衣柜,桌子上放着一台老式的电视机。他把背包放在椅子上,走到窗边,推开窗户,雨还在下,桂花树上的水珠顺着叶子滴下来,落在院子的石板上,发出“嗒嗒”的声音。